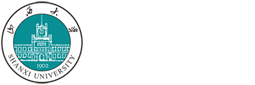时间:2022-07-22 信息来源:校友办 作者:李闻莺(新闻系2003级校友)
很荣幸能在母校诞辰120周年之际,与各位师长、校友“纸上会面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与同龄人相比,我的身份、地位、所取得的成就,远远谈不上出类拔萃。之所以有这样一次分享,我想,很大程度是基于自己在追求“新闻”这条路时有一些还算丰富的体验。从事新闻工作已十二个年头,坦白说,这不算一条光明大道,但亦有别样风景。它赋予我的酸甜苦辣如此真切,人生也由此感到丰盈充沛。
我的大学生涯与大多人别无二致。不是班干部也非社团活跃分子,成绩不好不坏,最高奖励应该是二等奖学金。尝试了恋爱、收获了友谊、翘过课甚至还莫名其妙挂过一门选修。偏爱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这两门课,却在古代文学课上看小说被老师发现出了糗。同时也是忠实的“上自习爱好者”,当年的文科楼占座之火爆记忆尤深。

时间的滤镜下,本科四年平淡美好。如果一定要寻找一点深刻的成长烙印,还要从大三暑假决定考研说起。此前很长一段时间,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,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年少时“铁肩担道义”的侠气。后来一度成为体育赛事迷,再加上喜欢魔都这座城市,上海体育学院新闻系成了我的目标。
不过,因为单科成绩几分之差,第一次考研失利了,之后我考上“大学生村官”,成为太原某城中村的村委会主任助理。那段日子我有些郁郁寡欢,但也不确定是否继续考研。毕竟,在旁人眼里,这份工作尚可,离家近、相对稳定,真正迈入“体制内”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但我内心又无法完全说服自己,犹豫中,有个人对我讲了一番话。
她是我所住小区的社区干部,高挑、美丽,每次见到都是精致的妆容、得体的服饰和自信的神情。有一天我们在小区碰到,听说我在当村官,她有点惊讶,告诉我不能打发日子,要找机会去做真正喜欢的事情。她说年轻是资本,才华是资本,还可以去拼的时候,不要错过每一个机会。
那是我在安逸环境度过半个月后,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、经历更精彩的人生。离开时,她祝我好运,讲了很多次,表情恳切,也许夹杂着一个女人年轻时未完成的梦,也许是把曾经的遗憾转为希望给我。
离开还是留下来?要眼前的稳定还是未知的梦想?20多岁时,我不止一次面临这样的选择。
后来我如愿考上研,却没有很快踏入媒体行业。从上体毕业后,大概是恋家,又或是有几分求稳的念头,我选择回到太原,进入山西一家出版社担任编辑。
正值暑期,出版社办公条件相对简陋。几位编辑老师摇着扇子伏案工作,其中一位看着作为新人手足无措的我说,“你都出去了怎么又回来了?”
那位编辑老师和我交流了不少,大意还是要出去,夹着几分抱怨、几分提醒。懵懵懂懂上了半个月班,杭州电视台的offer来了,纠结数日,我决定南下。
刚到杭州仍不够坚定,收入微薄、也不习惯漂泊,还要和比我小几岁的房东“斗智斗勇”。于是我又去参加过几次“体制内”的招聘考试,还考上了山西某院校的教师。学校虽然无法和山大、理工相比,但在当年也有一番前景。体面的身份、令人羡慕的寒暑假,必须承认,我有些心动。
经历了无数次挣扎,征询了身边很多人的意见,甚至抛过几次硬币,我咬牙拒绝了教师工作。至今记得打电话告诉学校工作人员时,对方语气带着诧异,说你想好了啊,这批只有你一个放弃。
自那之后,我知道唯有一路向前,从电视台到报社,从杭州到上海。不知前方是什么,能确认的只有一腔热忱。
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,必将经历很多挑战。澎湃新闻刚上线那两年,我做的是反腐报道、监督报道,为有所斩获,可以说“竭尽所能”。
记得在东北一个小县城,因为拿不到核心内容,绝望地想回去要不要辞职;也记得稿子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发表,气得嚎啕大哭;还记得为了拓展一点人脉,在陌生的饭局喝酒再喝酒。
采访中有时不得不隐瞒身份。曾独自一人打车,去离县城还有几十公里的小村庄,和一对老夫妻聊到晚上8点多。临走时我才拿出名片,老太太愣了一下,没有责怪,但我能从她沉默的几秒钟里感觉到一丝迟疑。
几天后,我去见另一个人。他80多岁,是非常重要的知情人士。我太想得到信息了,聊了一下午,从头到尾都没告诉对方我是干什么的。一个月后,稿子发了,我给他打电话。电话那头,老人说,我猜到你是记者了,稿子我看了,还算客观。
愧疚涌上心头,我掉了眼泪,自责怎么能利用一个老人的善良?一度打算不再撒谎,但也意味着失败率提升。比如我曾花一个星期打听到某位官员可能出现的地方,用2个小时等到人,听说我是记者,对方慌张逃走了,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指着我问,你什么意图?
我能理解对方的顾虑,类似的情况也遇到不止一次两次。某一刻会委屈,但又告诉自己这是职业行为,我没有恶意,如果一个事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连“冰山一角”都无法看到,又有什么资格自诩为“甲板上的瞭望者”?
于是那些年,我和我的同事总是出差在路上,习惯被拒绝,常常被误解。我们都有过类似的心情——手握一长串电话号码,却不敢轻易去拨打。因为电话断了就相当于线索断了,结果来临前,要尽力做好各种预案。
一线采访也让我学会了接受现实——想做好一件事,必须全力以赴,但并非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。
所以当报道赢得认可、拿到重要奖项以及获得个人荣誉,我都认为是自己运气足够好。后来,幸运女神把这份眷顾带到了全国两会,让我拥有了作为时政记者的“高光时刻”。
那是2017年3月15日,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。时隔五年再回忆那天有些模糊,只记得天不亮就起床出发,赶到会场已有不少同行在等待。
我的位置并不显眼,每一次提问更要高高举手。终于,机会来了,工作人员把话筒递来。我向总理抛出提前准备好的问题——根据网上投票,2131万网友都很关心“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”,请问准备如何解决这一问题?
总理反问我,你讲的这个问题排在第几位?听到我回答“第一位”,他接着说,有恒产者有恒心。对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续期问题,国务院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做了回应,可以续期,不需申请,没有前置条件,也不影响交易。
习惯幕后工作的我就这样站到了“台前”。因为是直播,人还坐在金色大厅,手机就迎来“狂轰滥炸”。连续半个月的两会报道令人精疲力竭,记者会结束后,我回到酒店狂睡一个下午,醒来时手机有上百条信息。
毋庸怀疑,这次提问之于我、之于澎湃新闻,都具有特殊意义。这是澎湃新闻记者第一次在全国两会获得提问总理的机会,但同时我也有些惶恐——好的记者用作品说话,而不是把本人置身于聚光灯下、满足于表面的繁华。
应该说,对记者来说,提问是一项必备技能,只不过有些是公开的,有些是私下的。面对敏感议题,有人开诚布公,有人避而不谈。因为问题过于犀利,我还被投诉过。每一次提问都是珍贵的,特别是在全国两会、党代会这样的重要场合,它们就像观察中国政治、经济的“窗口”,透过这扇窗,我寻找答案、捕捉细节,看到的是一个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错综复杂又生机勃勃的一面。
从事媒体工作的第九年,我从记者转为部门主编,职业生涯进入另一种“在路上”。这些年,媒体行业起起伏伏,有人冲着光荣与梦想而来,有人带着百感交集离开。
我不再高举所谓“理想”的旗帜,更多时候认为自己是一个“记录者”,仍追求真相,但也清楚不是所有的真相都美好,世界也不是每一刻都会对你温柔相待。媒体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信息需要流通,而信息中承载的文明、思想和进步。
迟疑或徘徊时,我会想起在几年前在香港某家茶餐厅,翻开新买的一本书。
作者在文末写到,“面对明哲保身的自得其乐、犬儒主义的冷漠、胆怯带来的妥协、玩世不恭的高谈阔论以及纯粹的邪恶,那些源于高尚勇气和理想主义的行动——或者仅仅是纯朴的正义行为,仍在昂首前行,不时为失望中的黑暗燃起灯光。”
这段话曾让那个午后的心情明亮汹涌又澎湃。在此与各位师友共勉。